小编: 人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形形色色的加工?为什么会高度关注身体表面的状态?衣服承载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意义,它是我们的社会皮肤,是我们的自我表达,有时,甚至是我们的自我本身
人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形形色色的加工?为什么会高度关注身体表面的状态?衣服承载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意义,它是我们的社会皮肤,是我们的自我表达,有时,甚至是我们的自我本身。《衣的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透过衣服,观察内心的视角。
近日,第40届开罗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埃及女演员拉尼娅·尤塞夫因身着黑色镂空长裙而面临起诉。起诉者认为,尤塞夫的着装“不合社会价值且影响埃及女性声誉”。尤塞夫道歉称:“我对这件衣服的预期出了偏差,如果我知道会是这样,我一定不会这么穿。”据英国媒体报道,她已被告上法庭,可能将要面临长达五年的刑期。
这一事件与埃及社会传统对女性的偏见有关,不过,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这或许证明了加拿大哲学家麦克卢汉

衣服其实承载着相当重大的意义。强迫某个人穿某一种衣服,可能会对那个人造成伤害。反之,自己穿的衣服也有可能伤害别人,或者引起社会的反对。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若从相对简单的视角来看,穿衣的举动与每个人的自我生成有着莫大关系。
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衣服。但人为什么穿衣服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也并非那么简单。日本哲学教授鹫田清一认为,穿衣的学问是一门哲学,它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穿衣”行为,比如化妆,比如染发,比如使用香水。在这一切背后,是一种名叫“时尚”的东西引导着我们的行为。
时尚撼动着我们关于身体的观念,它总是在戏弄人类最严肃的哲学主题:“我是谁?”但它又总是被认为是肤浅的。身为哲学领域的研究者,鹫田清一最初因为研究衣服与时尚遭遇的阻力相当之大,甚至是侮辱和嘲笑。刚写完第一篇时尚论,他的老师就对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一书中对时尚杂志进行的语言分析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真是世道不古。”看似在批评罗兰·巴特,其实是含沙射影地指责他。这段令人伤感的记忆使他至今难以忘怀。
衣服明明是生活的必需品,但人们却瞧不起服饰与服饰的流行,认定这是肤浅的,是表面文章,不愿将其纳入更深入的研究中,在鹫田清一看来,这是一种误解。因此,在《衣的现象学》这本书中,鹫田清一努力为“时尚”正名,也为我们揭示了衣服与自我认知的深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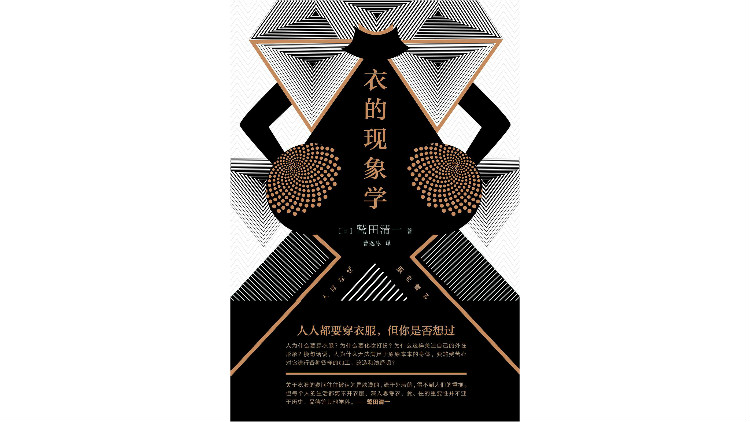
《衣的现象学》,作者:(日)鹫田清一,译者:曹逸冰,新经典·新星出版社 2018年10月
要回答“人为什么穿衣服”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把衣服是用来保护身体的观点搁置一边。衣服常与人的外表画上等号,但我们不能完全把它当成“披在身上的东西”,需要抛开功能性这种固有观念,重新审视人的衣装。如此一来,看似有违常理的问题就会立刻浮出水面:为什么人要想方设法折腾自己的身体?
让我们从头到脚往下看。人要梳头,把头发烫卷。有时还要编复杂的发辫,或故意弄湿。胡子是要刮的。眉毛也得刮,刮完了还得重新画。眼睛周围要描上深色的线条。脸颊要涂白,嘴唇却要抹成红色。牙齿不齐的可能要矫正。在耳垂上穿孔,把耳环穿进去。在颈部缠上链子。指甲上要抹油漆似的指甲油。手上要戴戒指或手链。腋毛要拔掉。从肩膀到膝盖
要裹好几层布,布料的形状还相当复杂。给脱掉多余体毛的双脚裹上透明织物。如今还有人在脚趾甲上贴五颜六色的甲贴。把双脚硬生生挤进材质坚硬,不合脚形的皮鞋。有的人还会在皮肤上文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加工身体的花样简直多到让人感叹。
人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形形色色的加工呢?为什么会高度关注身体表面的状态呢?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身体有所不满。拿自己的身体和某种现行标准,也就是社会的标准或典范做对比,就会发现一些差距,进而提高对身体的关注。这恐怕也是我们格外在乎投向自己身体的视线的原因。如此看来,人为什么要穿衣服的核心是人无法满足身体原本的样子,要煞费苦心进行各种各样的加工、改造和演绎。
但这问题绝不仅限于衣着领域。把“加工身体”诠释得更宽泛些,就成了语言、行为表情等使用身体时需要面对的共通的问题。
洞,都有一部分‘自我’脱离身体,感觉身体越来越轻盈了。”这是某社会学家街头采访时一位受访者的回答。人往往会被固有观念束缚,被束缚在身份的桎梏中。穿孔时,我们感受到摆脱它们的轻松,切身体验到身体有形形色色的变化可能。也就是说,打耳洞引领我们品尝了一种小小的怦然心动——身体的确是灵魂的载体,但这个载体是可以改变的!要是能像脱衣服那样把灵魂的载体脱掉,那该有多好。甚至可以说,这是藏在大多数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再三伤害自己的身体。

也许我们还能将穿孔看成一种“离巢仪式”。身体是来自父母、顺应自然的存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意味着主动解除了亲子间的自然纽带,向父母宣布:我的身体我做主。其中也有某种被逼上绝路的情绪,毕竟我们能真正自主掌控的就只有这具身体,似乎不伤害一个人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身体,就无法切实确认自己的存在。
每个人都认为身体是世界上最贴近自我的东西。可细细琢磨就会发现,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其实少得可怜。比如,我们只能直接看到身体正面的一部分,不借助外物谁都无法看到自己的后背或后脑勺。要命的是,别人主要依据脸辨认我们,可每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直接看到自己的面孔。同时,不受控制的情绪与心情偏偏会表露在这张脸上,完全无法防备。
身体表面已然如此,发生在身体内部的零碎变化,就更加无从得知。心中油然而生的欲望与情绪也是很难掌控的。疼痛与疾病总是偷偷袭来,而我们时刻处于等着挨打的状态。对人类而言,身体无异于不稳定因素的温床。我们无法全方位感知身体的状态,更无法自如掌控它的方方面面。如此看来,人与身体的距离远得超乎想象。正如尼采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的一句德国老话:“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

《古怪的身体》,作者:(日)鹫田清一,译者:吴俊伸,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
人永远只能靠想象揣摩自己的身体。身体在我们眼中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形象,不过是想象的产物,能被自己掌握的信息少之又少。所以这个形象很容易被动摇,一碰就碎。为了加固脆弱的身体形象,我们在生活中摸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技巧。
美国心理学家赛默尔·费舍尔在其著作《身体的意识》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他认为,泡澡或淋浴之所以让人觉得舒服,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会持续接触到和体温有温差的液体。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皮肤的感觉被激活了。平时无法通过视觉了解的背部轮廓因为皮肤感觉活化变得清晰。换言之,人们能通过洗澡强化身体的感官轮廓,使自己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界线更加明显,存在形态更加确切。

三宅一生,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在他的作品中,衣服与身体之间留有大量空隙,松弛自由,人似乎在以衣服为媒介,和身体对话。
衣服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它几乎是加强人体轮廓感知最常规的装置。人的每一个动作都会造成衣服和皮肤的摩擦,为皮肤提供适度的刺激。这样我们就能以触觉确认视觉无法感知的身体轮廓了。衣服就这样悄悄平息着由于身体的难以把握而潜藏着的焦虑。
衣服对身体表面施加持续且适度的刺激,不断加强人与身体零碎且模糊的轮廓感知。正因如此,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衣服称作人的第二层皮肤。事实上,一旦如此,“自我”的表面就会转移到衣服上。衣服里面就是自我,要是有人把手伸到衣服里来,我们就会不由得打哆嗦。在他人面前脱衣服不单单是卸下多余的遮盖物,还伴随着强烈的情绪波动,仿佛在揭起自己的皮肤,又仿佛一片片剥下自我的存在。
身体对我们来说是想象的产物,正因如此,人才会产生身体出错的感觉,就像不小心穿错了衣服,做整容手术、变性手术、尝试异性装扮……这些人十有八九是认为自己的身体与存在不完全相符。
如果每个人的存在从根本上是靠某种想象支撑的,我们就很有必要用同样的观点去审视穿衣与化妆。毕竟这是在离身体最近的地方展开的,是对存在表面的加工或改造。法国文学评论家贝多万在《面具的民俗学》中说,穿衣与化妆是对人存在的形象进行加工改造,以修正存在本身的尝试。通过改变自身的物理形态改造内在以突破自我极限的欲望,时刻不停地刺激着我们。

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剧照。图中是身着风衣的里克在与伊莉莎话别。
在近代城市,人永远是个体的、独特的存在;而且必须在社会中拥有可识别的、明确的身份地位。乔装假扮会模糊这种存在方式,所以除了狂欢节、舞会等特殊场合,都是被世俗禁止的。于是,脸就成了书写记号的平面。此处的记号,指的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性格。一张没有作假的、裸露在外的脸,就是一个人的素面。为了让这张脸显得更好看,或者说,为了假装这是一张没有动过手脚的脸,人们用复杂的方法给脸部画上精致的妆容。为了展现自己的脸,更直白一点,为了依照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人们投入巨大的资金给自己“整容”。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女性会想方设法掩饰自己化了妆的事实,假装天生就长这般模样。现在大受追捧的“裸妆”就基于这一理念。然而在人类社会与历史中,这类妆容并非十分普遍。
生活在撒哈拉的沃达贝部落有举办舞蹈大赛选美的习俗。参赛者是男性,评委是女性。男人会把发际剃干净,上妆突出自己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再用颜料把脸分成好几个区域,每个区域一种颜色。最后戴上用于驱魔的项链。上场时男人们对着女评委瞪大眼睛,变着法子使眼色。为了让自己显得更高,还会脚尖点地,身子不住地前后摇摆……这样的场面发人深思,原来把所谓的“裸妆”当成化妆的常态,明明化了妆,却要假装自己天生如此,是落入了天大的误区。

现在,不刻意隐瞒化了妆的样子似乎打破了“伪装式化妆”的悠久传统,在我们周围逐渐普及开来。所谓的“恶趣味妆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把头发染成茶色或金色、重新画出来的细眉、蓝色或黑色指甲油的流行都属于这一范畴。
但化妆也有独特的医学功效。化妆心理疗法成了当今学界的一大热点,好几所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室都在重点研究这一课题。通过化妆
疗愈面部受伤的人,为切除乳房的乳腺癌患者研发专用内衣,从侧面帮助她们重新构筑自我与身体的关系。
涂抹、加工身体表面曾有类似宗教仪式与科学研究的强大力量。当然,此处的宗教与科学是一种技法,用来把握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曾几何时,科学就是帮助人们把握肉眼看不见却推动世界运转的规律的。化妆和服饰也有同样的作用,而且它们和宗教修行、冥想与舞蹈一样,都用于捕捉可感而不可见的东西。身体是用来感受世界的,因此人们要对它进行各种加工改变。化妆虽然是修饰仪表的技法,但从词源上追究,这个词其实含有“宇宙”的意思
(“化妆”一词的英语“cosmetic”和“宇宙”的英语“cosmos”词源相同)
然而,脸逐渐失去了朝向世界外部的功能。法国评论家罗歇·凯卢瓦说,近代的颓废,始于面具的衰退。脸失去了“作为脸和面具”的双重意义,仅代表个人符号。与此同时,化妆和服饰也不再是变身与沉醉的手段。用墨粉、胭脂、矿石、金属与彩漆装饰表面
,而是成了针对他人,即隶属同一社会其他成员的诱惑和表演,成了细微调整人际关系以及在一定规则中表现自己小小叛逆的手段。
哲学家米歇尔·塞尔曾在著作中写道,皮肤是人类的表层感官,会形成褶皱,出现相互接触的部分。这个部分正是灵魂居住的空间,所以刺青与涂饰等化妆手法的历史都能追溯到太古时代。化妆本该是用心倾听分散在皮肤各处的灵魂的过程,只有被装点得漂漂亮亮的耳朵捕捉到的时候,灵魂才会发出清澄的回响。可见,化妆是装点我们对世界感受的手法,是对宇宙的一种诠释。
话说回来,面孔着实不可思议。它不仅是自我的标识,有时甚至可以成为自我本身,我们却绝不可能直接看到自己的脸。也就是说,脸和自我的距离无限遥远。这与之前所说的身体与自我的距离无限遥远如出一辙。

川久保玲,日本服装设计师。博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定义“所有符号都会被囚禁在拘泥于相对关系的流行地域”缝进了川久保玲的衣服里。
有一句老生常谈:衣服是人的第二层皮肤。不过大多数人只把它看成一种比喻。麦克卢汉认为,我们应该把衣服看成皮肤的延伸。因为它既能调控温度,又是社会生活中自我界定的凭据,是一种“社会皮肤”。精神分析学家E.莱蒙恩-卢奇奥尼把这句话改成“衣服是可以穿脱的皮肤”。如果衣服等同于皮肤,那么反过来说,皮肤等同于衣服也是成立的。因为我们无法完完整整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只能感知到零星的碎片。在想象层面将这些零零碎碎的知觉形象拼合成一个整体,才真正拥有完整的身体。这其中的关键是拼合。
如果拼合而成的自我形象是我们身披的第一层衣服,那衣服就不再能包裹我们了,说它是存在的接口、合页似乎更合适。更直截了当些,衣服其实是身体的第一属性。将身体形象看作身体的第一层衣服,像撕扯布料一样撕开、抓破皮肤,在上面描画、涂抹颜料、埋入异物等行为才有比编织纤维更悠久的历史。所以皮肤中其实有接缝,也有纽扣。缝住女性生殖器的习俗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现代也有人特意用安全别针固定自己的阴唇。在这些人眼中,这种行为与在耳垂、鼻子、嘴唇、乳头等部位穿孔没有区别。
人们通过不断对自己的身体施压获取自我脱落的感觉,这是一场与自己的交易,交易者主动送上某种无偿的
负荷,甚至可以将这种负荷称为施加给自己的小暴力,换取精神层面的报偿。这种行为与宗教很像,只是缺少一个组建的契机罢了。
在E.莱蒙恩-卢奇奥尼描绘的医院景象中,也能找到与上述行为相近的举动:精神病院的疯子经常乱穿衣服,而且都不把衣服好好固定在自己身上,成人帽或童帽是斜着戴的,裙子系歪,鞋子更是左右颠倒,纽扣也不会扣好——无论是衣服的纽扣,还是皮肤的纽扣。光是乱穿衣服,患者还不过瘾,他们连自己的皮肤都不放过。抓、剩、撕……想尽量脱得干净些。通过折磨、约束身体获得救赎。正是因为皮肤
就是自我,这种感觉才如此明确,我们很可能在戏弄身体形象的时候,打了一个关于“我是谁”的赌。借用罗兰·巴特的说法,这正是一场赌上身份的游戏。

既然这么重视皮肤,为什么又要对皮肤百般折磨呢?因为皮肤是感知世界的装置,关于“我是谁”的信息经过皮肤传输。皮肤不是自我的围栏或遮盖物,也与胎盘之类的人体部件不同,因为它不是隔离主体的膜。皮肤这层薄膜会对通过它的信息进行筛选,筛选机制会改变通过皮肤的物质的形态,将精神性的转变成物理性的,与性别无关的转变成与性别有关的。如变压器般将细微的信息增强,转化成肉眼可见的形态。我们的自我恐怕就存在于这种转换意识之中。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细细琢磨现代的衣服,就会发现内衣与外衣的区别正越来越小。人们愈发青睐不再通过区分私密与公共等身体故事“向皮肤发出细微呼唤”的衣服
,内衣则有逐渐消失的趋势。讽刺的是,这种趋势越是明显,曾被用在内衣生产中的经验知识就越有用武之地。真丝般的触感、可伸缩布料特有的弹性……长久以来,内衣设计始终专注于肌肤感受。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无限接近衣服的本质定义,即人的第二层皮肤。皮肤的可变时代说不定已经拉开了帷幕。在高科技材料与对皮肤想象力的互动中,比每个人的自我更古老的灵魂,又或是我们自身的野性似乎正在蠢蠢欲动。
很明显,时尚给出了他人对自己形象的期待,也给出了自我形象的模板。时尚怎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代表着独立个人出现在人群中时呈现的样式。请注意,一个人只能在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确认自己的身体。其他人能直接看到我们的脸,而这是自己不可能做到的。自己的发型、身体的轮廓、举手投足的仪态都无法得到直接确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看得见、摸得到或听得见的若干身体部位和别人的眼神反馈的信息、镜子或照片中的影像等片段化的信息拼凑起来,用想象力的丝线缝补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是我们和自己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没错,还要考虑到自行拼凑的身体形象与他人印象存在怎样的偏差
被深度植入社会共同体并在其中生活的时候,还可以在某种强大稳固的框架中勾勒上面提及的自我形象,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今时今日的我们无论是否情愿,从出生的那一刻就与社会所有方面自动相连,深深嵌入其中。每个人都必须不断选择外表与举止样式,并将它们变成自己的血肉,存在样式就这样在社会的庞大神经组织中组装起来。时尚为我们提供了组装的模板。当然,时尚不仅限于外观与举止样式的范畴。如前所述,时尚与个人身体状态的形象化全局密切相关。所谓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看、摸、听这些行为的集合与媒介,所以时尚也会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与感知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感觉均发生在身体表面,服装、化妆与身体表面直接相关,也就自然会与所有的感觉发生关联。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时尚就是发生在人身体表面的自我幻想与社会的第一次邂逅。
当前网址:http://www.sx-news.com/shehui/2018-12-06/69462.html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陕西新闻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